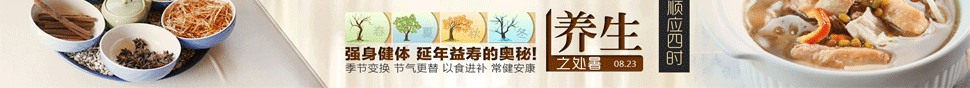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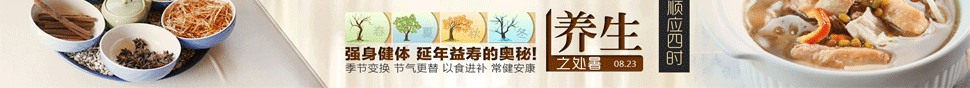
茶·酒·诗
will酒精也许是人最大的敌人,可是圣经也说了,要爱你的敌人。
———弗兰克·辛纳屈
凡使人上瘾之物,初次相遇后,遂成永远也戒不掉的情人,重点不在于怎么戒掉,而在于哪一款更符合你的口味,其身上的独有特征,即为能否被青睐的关键。
何时饮
T:看风小榼三升酒,寒食深炉一碗茶。
W:带酒冲山雨,和衣睡晚晴。不知钟鼓报天明。梦里栩然蝴蝶、一身轻。
T:游罢睡一觉,觉来茶一瓯。
W:唯愿当歌对酒时,月光长照金樽里。
T:举头中酒后,引手索茶时。
W:人生得意须尽欢,莫使金樽空对月。
助文思
T:三碗搜枯肠,唯有文字五千卷。
W:俯仰各有志,得酒诗自成。
T:起尝一碗茗,行读一行书。
W:一杯未尽诗已成,涌诗向天天亦惊。
与君饮
T:趁暖泥茶灶。
W: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。
T:应需置两榻,一榻待公垂。
W:相逢意气为君饮,系马高楼垂柳边。
增修养
T:从心到百骸,无一不自由。虽被世间笑,终无身外忧。
W: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,心远地自偏。
致生活
T:夜茶一两勺,秋吟三数声。
W:酒醒只在花前生,酒醉还来花下眠。
为红颜
T:湓江江口是奴家,郎若闲时来吃茶。
W:舞余裙带绿双垂,酒入香腮红一抹。
W(微醺):等等,还有,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
哲与思
W(已高):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。挟飞仙以遨游,抱明月而长终。
T:……
古语有云:鱼与熊掌不可兼得,你更中意哪一位呢,清秀恬静的查姑娘,缠绵魅惑的玖小姐?答: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呢!
▼
万里茶香
Effy.Lin到武夷下梅村,正是夏至未至的时节。
一簇古村落立于武夷群峰深处的青山脚下,清浅的梅溪从上游蜿蜒而下,到这里平静如练。想起梅溪名字的来由,这里曾经夹岸数里广植梅树,当年柳永、朱熹等人经过此处时,必定闻见溪中落英缤纷,暗香浮动吧。村外农田井然,鸡犬相闻,远山氤氲葱郁,若不是有一条公路横贯南北,偶有乡间巴士驶过,我会以为自己置身桃花源中。
深春的阳光格外清透,摇曳着落在一条由卵石铺就,将下梅村一分为二的人工运河——当溪上,明晃得有些扎眼。在当溪汇入梅溪的尽头,跨立一座重修过的风雨亭,不言不语远眺山峦叠嶂。恍惚间,明清时期这个村落“鸡鸣十里街,日出千鼎烟”的情景似乎依稀可辨。
谷雨节气刚过,家家收好了春茶,这正是做茶的季节,或晒或炒,整个村子的空气里弥漫着清幽绵长的茶香。当溪南北是长长的廊道,形成两条古街,路面被岁月的脚印打磨得温厚光滑,街边店铺以卖茶居多,门板已经老旧斑驳。村民们一面经营着小店,一面还在挑拣最好的春茶,热情招呼远道而来的客人进店品茶,仿佛百年前的风貌从未被改变。沿溪架设的“美人靠”上挂晒着表情慵懒的衣物,老人和孩子在这里怡然自得,静谧的画面,让人难以和“康熙19年,武夷岩茶茶市集崇安下梅,每日行筏三百艘,转运不绝”(《崇安县志》)的繁华往昔联系到一块。只有当溪中那九个已被藤蔓和苔藓覆盖了的码头,还在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人头攒动,船只络绎往来,无数妇人曾经倚在美人靠上择着茶目送丈夫运茶远行。
和丝绸之路齐名的万里茶路是一条繁荣了两个半世纪,如今湮在历史中的古国际贸易通道,起点就是当溪尽头那座被称作“祖师桥”的风雨亭。下梅,是一个因万里茶路而盛,又因万里茶路而衰的村庄。
邹氏是当地的一个大姓家族,当年邹家四兄弟从江西辗转而来,在下梅村落脚,勤恳种茶卖茶,山西晋商常家虽远隔千山,但灵敏地闻到商机,冒着生命危险南下,和邹家开始一百多年的诚信合作,联手开拓了万里茶路,将茶香撒播到万里之外。
茶成就了邹氏宗族,如今依然气势恢宏的邹家宗祠、精致考究的联排宅院大夫第、曾经是吟风咏月之处的小樊川、载着水榭亭台的西水别业,无不彰显昔日主人的荣光。我有幸在晋商曾无数次驻足的茶室中坐了一下午,和邹家后人把盏话茶。庭院的天井里种着一盆盆兰花,收足房檐倾泻的阳光和露水,墙砖青苔,似乎都带着水气,温润沁凉。
邹家三十代的少东家是一个年轻女孩儿,前不久以复原度很高的传统的婚礼轰动当地。品茶间隙,她母亲热情地拿出照片让我欣赏,当溪两旁的廊道挂满红绸和灯笼,溪中运着殷厚红妆的竹筏上,一对着龙凤盛装的新人坐立船头。这幅画面瞬间让我联想到百年前,邹家兄弟也是这么迎娶那位相传丈夫出行后在美人靠边望穿秋水,最后化作鲤鱼的夫人吧?心里正感慨着,这位少东家外出归来,跨过门槛,向我们浅笑,身上的青绿麻衫仿佛茶汁染出,和古老的建筑融为一体,飘然若云。
村里有许多狭长的深巷,寂静无声,高大的马头墙后,若隐若现的不知是谁家小姐的闺房。当年也许是随意种下的山茶桂花,如今都长成大树,惹得我们这群不速之客都想一探究竟。
村里不停歇的炒茶声伴随着温暖的芳香,村外的田野将醒未醒,在缓缓漫过的水渠里舒展。炒一盘野菜,对着窗外梅溪掀起的一阵阵凉意,想起朱熹那句“晓登初移屐,寒香欲满襟”,真想抱一坛村民自酿的杨梅酒,沉醉在此不复醒。
茶—浅浅阅
云雀茶属山茶科,据考证起源于上古时代的中国西南地区,以云贵川为核心,各地共有余种四系:五宝茶系、五柱茶系、秃房茶系、茶系。《中国茶经》将茶分为绿茶、红茶、乌龙茶、白茶、黄茶、黑茶六类。经过历代人民的培育,形成种植、采摘、制作、品鉴和各种礼仪规制的茶文化,衍生出的茶器、茶礼、茶食、文学艺术作品和品牌不胜枚举,经久不衰,远播世界各地。
茶是人在草木间。每当看到茶叶店里的龙井、毛尖、云雾、铁观音、猴魁、大红袍、黄金芽、普洱......足以激发人的想象力,勾勒出它们长在茶树上的样子。仿佛看到辛勤的采茶娘子,在漫山的茶园,用灵巧的手指将茶叶一片片收入茶篓,用炒茶师傅的技艺将叶片中的香气缓缓激发出来,装在各色精美的茶皿中,伴随着悠扬的古曲,洗茶、冲泡、品茗、读经、开悟。饮茶分四季:春饮花茶、夏饮绿茶、秋饮青茶、冬有红茶;日有早茶、下午茶、晚茶。也分地域:北冲黑茶(茯砖),东品白茶,中啜黄茶。总有一款抚心慰肠,日子妥帖了起来。渐渐聚齐了开门七件事:柴米油盐酱醋茶,茶愈发不可或缺。
自幼生活在西北干旱之地,阳光炽烈,雨水稀少,棉花小麦葡萄西瓜产量高质量好,独无茶,于是对茶充满了神秘和想象。仰仗着茶马互市和丝绸之路,西域许多民族也养成了喝砖茶的习俗。砖茶以各种茶叶做基底压制而成,有黑砖、青砖、米砖、臧茶、茯砖、邮票茶(第一次听说)等之分。湖南益阳砖茶没有一般茶叶的模样,黑硬的长方形茶饼,得用很大的力气才能一块块掰开。“宁可一日无食,不可一日无茶”。将其与牛奶加盐慢慢熬煮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就着主食和肉类,喝碗热乎乎的奶茶,祛除劳作的疲惫与寒冷,补充维生素,“茗者八方皆好客,道处清风自然来”。儿时曾在杂志上一睹茶花的绚丽多姿,就常渴望去南方的茶园采茶,体验一把茶农的生活,想必别有一番滋味。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。寻常一样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”。北寒之地,冬日漫长,一杯热茶,天地流转,风不烈,雪亦暖。
遇见精致的茶器,眼前会自动闪现下午茶的场景:在美丽的后花园,圆桌上摆放着小甜点和一壶红茶,白色的茶盏镶着金边,勃朗特姐妹围坐在一起边,边热烈地讨论着自己的作品。也像美国女诗人艾米莉·狄金森常在夜深人静时的窗边小桌写诗:“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,我本可以忍受黑暗。”桀骜不驯的她有茶相伴,灵魂在文字里起舞,仿佛茶在暗夜里的回响。
“茶起禅空香自在,琴鸣道妙韵天成”。那日午后,窗外沙沙的雨声一直萦绕在耳边。云低雾霭。冲一杯茶,绿色的叶子在杯中翻滚、舒展,渐次释放出层层绿意,茶香弥漫,热气蒸腾。此刻,魂游天外。
不如吃茶去
不如吃茶去“山水之间”
年,许嵩出了一张专辑《不如吃茶去》。这整张专辑所有的歌我都特别喜欢。“大千世界有很多想不通的事、猜不透的心与看不透的人,倒不如不想、不猜、不看,携寄情山水的快意人生吃茶去”。
昨夜同门云集推杯又换盏
今朝茶凉酒寒豪言成笑谈
半生累尽徒然碑文完美有谁看
隐居山水之间誓与浮名散
(主打歌《山水之间》的歌词)
许嵩想通过这一张专辑,表达淡然的人生态度。如今这个时代,潜心做音乐的人凤毛麟角,更多的是流量变现,不可持续的流量在我看来毫无意义。
“空持百千偈,不如吃茶去”
据典传,有僧人问雪峰义存禅师:“古人道,路逢达道人,不将语默对,未审将甚么对?’’禅师答曰:“吃茶去。”又据传,有唐代高僧从念禅师,人称赵州和尚,每次话前总要说“吃茶去”,有两位僧人至赵州和尚处,和尚问其中一位:“新近曾到此间么?”,答“曾”,和尚曰:“吃茶去!”。和尚又问另一位僧人:“新近曾到此间么?”,答“不曾!”,和尚还是曰:“吃茶去!”。
即使参悟透这世间所有的真理,真不如一杯茶给人带来恬静悠闲的美好时光。
“柴米油盐酱醋茶,琴棋书画诗酒花”
生活不能仅仅是柴米油盐酱醋,也需要琴棋书画诗酒茶花。除了物质生活之外,更需要精神世界的丰盈。希望你我能够品尝到生活的酸甜苦辣咸以外,也能够拥有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的淡然雅趣。
▼
茶
华仔作为年轻人,其实接触茶不算多,我可能更喜欢喝的是酒。
大学毕业以后,来到南方,很潮湿很热,舍友推荐雪菊,买了茶具,我跟茶的接触也就开始了,至今了解的也不多,之前随便读过一本介绍茶的书,算是稍微了解了一些吧。工作原因,我喝酒比喝茶要少很多,所以很多记忆都也和茶有关。
成都,人民公园或是小剧院或是随便一个大院子,一碗茶,掏个耳朵、看看变脸,找老外聊聊天,或者就喝茶,消磨时间,享受宁静。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小知识,比如在茶馆喝茶,要出去吃饭或者出去一下,可以把茶碗的盖子放在做的藤椅上,这样人家就知道你还会回来了。
宏村,山坡旁,露天的二楼,阳光和煦,微风拂面,两人相对而坐,一本《过于喧嚣的孤独》,一壶茶,一小瓶果酒,阳光透过竹帘洒在人的脸上、衣服上、书上。此生难忘。
虎丘,半山腰,冷香阁,四面皆树,临窗而坐。以后定要找一人一起去喝茶的。
拉萨,喜鹊阁或者随意的茶馆,更喜欢酥油茶,躲避镜头的可爱的红脸小孩子,坐我对面,拿刀切生肉给我吃、请我喝他们自己带的酥油茶的语言不通的老夫妇,喝着酒玩着当地筛子的两个林芝老哥。自在、惬意,会忘记一切。
石家庄,书友的朋友,请我吃饭、请我喝茶、给我讲茶、送我茶的开茶店的姐姐。萍水相逢,平淡如水,我竟喝醉了。
郑州,拜访老师,安静的茶室,喝到闭馆。我也长大了,遇到好老师是件极幸运的事。
单位宿舍,两个好友,一桌子零食,我带的茶,吐槽领导,谈论时事,谈最近读的书,可以聊到凌晨三点。一友难求。
赤道,七级风浪中的夜航,下着雨,一条小船,四个人,甲板上,实心铁的桌子和椅子,从下午喝到凌晨一点,脚下是温暖的海水,身上是寒冷的雨滴,从此,喜欢上了红茶温暖的感觉。
路还很长,期待后面的日子。
(台湾著名茶人解致璋的茶席)
茶之味忽忽我最初被茶完全俘获全因茶席之美。新搬来的邻人是一对上海夫妻,开了一家叫“小雅斋”的茶馆。那茶席的布置不同于内地的常见竹盘、紫砂的俗物,而是台湾与日式的茶席,那种清寂优雅的美感,我一下便被深深地吸引。小而精致的杯、古朴的壶、简素的茶巾,旧旧的古瓶中插着一枝绿枝,安静的空间里氤氲着茶香,一切都令我着迷。于是邻人日后便带着我这个痴人走近了茶。
见了许多的器,自己也收了一些器;也见了许多的茶席,自己也陆续添了一些喜爱的茶布;喝了一些茶,也开始认识各种茶的种类。但一切还停留在一个形式的美学与知识的层面,直到有一天我参加了苏州的一个禅修营。一位僧人模样的女师傅给大家泡了一款不知名的红茶,那茶的味道入口即化,明媚清甜,我不禁惊呼:好香啊,象秋天的少女!师傅朝我笑着点头,默默赞同。席间数人无一不留恋赞叹那茶香,数年以后,那美好的感觉成了我品茶的标尺,连同那一饮之间窗外的枫也成了记忆的幕墙。
从此,喝到好茶便会认真记得那个滋味。
再后来,慢慢跟着朋友学泡茶,从繁至简,从精准到自然,从刻意到无意,慢慢去体会茶后面那个“道”的境界。茶是个寄物,白先勇先生在讲红楼的时侯说,中国人其实最后大多数都会以儒、道、佛三种思想形式寻找心灵的家园。此次共读《中国茶文化》里也可窥其一斑。
读书是个越读越胆小的过程,仅仅一本茶书即见中国古代文化的璀灿幽深,陆羽与颜真卿的友情,历代文人的风骨气节都令人动容。而朴实的民间茶艺、生动的茶风俗文化又令人感叹生活的腾腾热气。
除去作者对西方文化隔应的感受与偏见,这本茶书还是相当全面地普及了茶知识的方方面面,加之自己偶读的一些补充读物,群里老师们细致的分享,书虽然还未读完,但对茶进一步系统地了解又多了一点信心。
谈茶
Effy.Lin喝茶好像是福建人的特嗜,从闽东到闽西,从闽南到闽北,茶馆、茶楼无处不在,三两成群坐在老街店铺门前沏茶攀谈的,也不在少数,走亲访友,更少不得搬出茶具对饮一番,仿佛到了此地却不感受一下当地的茶文化,便是一桩憾事。
第一次在茶馆里正儿八经地端着若琛瓯品茗,敛容屏气,正襟危坐,唯恐露丑。且不论杯中物滋味如何,《红楼梦》中妙玉调笑宝玉的那番话我可是记着的:“岂不闻一杯为品,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,三杯就是饮牛饮骡了。”面上要装模作样以免贻笑大方,内心暗忖那些文人雅士着实不易,连喝口茶也要讲求君子之风,我还是适合老老实实当个饮牛饮骡的俗人。
过去民间喝茶的方式很是粗糙,开门七件事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就包括茶,茶在国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,关乎民生,无关雅俗。清晨外出前丢一把干茶(方言谓之“茶米”)浸在搪瓷杯或陶壶里,归家时便可开怀畅饮。沏了一天的茶十分浓酽,舒展开的茶叶往往占足一半空间,我对这种大人们甘之如饴的饮料敬谢不敏,倒是喜欢用海碗从工人的大茶桶中舀着喝,茶味较淡,但茶汤甘甜爽口,在酷夏中尤其能慰藉舌本。茶碗从不消毒,人人都这么喝,也没听说过谁因卫生问题闹过毛病。或许是经济发展了的原因,讲究多了起来,近二十年来,那种细致的功夫茶道逐渐在坊间流行开,亲友聚会如若无茶,就少了些自在的氛围,茶俨然成了一种社交媒介。
我的茶龄不老,但和茶的缘分却是从小便结下的。家乡茶叶种植及贸易历史悠久,从记事起,每年春夏两季,家家户户都在采茶制茶,茶厂的机器日夜轰鸣,满城茶香。逢着无课的日子我还可以打零工赚些零花钱,孩子耳聪目明,挑拣速度不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可比的,积累下来的收获颇丰,但在我记忆中,印象深刻的始终是那一堆堆鲜嫩清香的茶青。
对茶我虽不敢谈品,喝却完全不在话下,可三日无肉,不可一日无茶,可以从早到晚不停歇,几乎不受醉茶、失眠等症状侵扰,即便因事外出数日,也必随身携带茶叶和简易茶具,以安抚嗜茶的舌苔。因为爱喝的缘故,倒是有幸喝过一些好茶,也有几次有趣的经历。
一日,好友相约在冯同学家里涮火锅,众人酒足饭饱后坐在电视机前嬉笑连连,我感觉口中浊腻,便向主人讨茶,冯同学在茶屉里翻找了半天,被眼尖的我瞧见一泡“雀舌”。这道茶我曾在两年前喝过,是武夷岩茶的一个小众品种,又名“不知春”,为古时贡茶极品,形似雀舌小巧可爱,气味十分独特清雅,用烧得正正好的沸水冲下,如幽兰绽放,满室芬芳,入口更是如花果绕舌,馥郁甘香。从此对其念念不忘,但据说产量低,也不是年年都有,求而不得,久而久之就成了我心上的一颗朱砂痣,如今无意间发现,怎能不让我欣喜若狂?果不其然,一开汤,屋里原本喧闹不已的众人顿时安静下来,不论茶客与否,皆向我讨要一盅——被这芝兰之气所吸引。次年购得同一款茶,虽然树种和茶师依旧,香气和滋味却与从前有了分别,说是气候和工艺细微的差别所致,但我想,心境恐怕是更大的影响因素。
还在上学那会儿,我的好友群皓每年夏天都会上山造访一位隐士,照片上碧水绿林茅舍颇有“富贵非吾愿,帝乡不可期”的风范,也邀请过我几次,但因种种缘由未能成行。工作多年后一个将雨未雨的下午,在栖云古寺和道良师品茗谈话,其间他特别提及那位隐士,言语中满是赞叹之意,当下便决定上山寻访,也算是对多年夙愿有个交代。正值初夏时节,天气有些闷热,沿着几乎没入野草落叶中的小石径一路向上,约摸一个多钟头后,眼前豁然开朗,一座质朴的土屋出现在竹林后头的空地上。恰巧群皓家人也在,我丝毫不生分,坐下便饮茶。在徐徐山风之中,一杯甘鲜清新的白鸡冠下肚,轻盈持久的冷香把我那被炙烤一路的燥热涤荡一空。白鸡冠属武夷“四大名丛”之一,叶偏白,呈黄绿色,带着发酵产生的红边,滋味甜沁,香气淡雅幽长,区别于大部分霸道、阳刚、厚重的武夷岩茶,是一个柔美的存在。过去我总有个误会,以为白鸡冠缺乏一股劲道,观赏价值大过品饮价值,在此露怯了。那晚夜色清明,我们在屋外空地上观明月缓缓爬上树梢,听蛙声换下蝉鸣,闻杯中茶香浮动,如入“半壁山房待明月,一盏清茗酬知音”之境,惬意至极!
又有一回到云南玩,顺道拜访一个微博上结识,聊过几次天的茶人小姑娘,她在丽江古城一条比较清静的街道上经营着一家茶馆。巧的是老板大哥刚从茶山回来,寻到一袋好茶,据说是一棵上百年的古树昔归,老板准备自留招待朋友,这会儿便抓出一把往紫砂壶里塞。那干茶条索十分漂亮,肥壮整洁,冲泡出的汤色明亮清澈,初入口时有苦味,但三秒后强烈的回甘如蜜似饯,让人身心舒畅,妙的是茶气虽重,口感却柔和细腻。正值春和景明,整座城市被花海淹没的季节,茶馆里光线通透,落地窗外垂柳摇曳生姿,很能营造品茶氛围。虽不敢与白乐天比肩,但此时此景真是想狂妄地道一句:“不寄他人先寄我,应缘我是别茶人。”
关于茶诗,宋人杜小山的《寒夜》是我所钟爱的——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。寻常一样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。茶固然可以独呷,但论情趣,恐怕不如与友人同享,清茶一杯,也可饮出浓厚情谊。想来那些文人雅士,也不过如此罢。
▼
《中国茶文化》读后感
刘艳中国茶文化,这个题开的本身就有点大。
而恰恰是这个宏大的噱头吸引我们想一探究竟。
通篇粗读下来,内容涉及庞大而泛泛,而留给群里讨论的更为有趣,有益。
我的家乡本不产茶,也少有人真正的喝茶(叶)。
但是,我们从学说话,渴了就要茶喝,先学会说“茶、茶”;白开水就叫“茶”,放了糖叫“糖茶”,暖水瓶叫“茶瓶”;杯子除了酒杯,都叫茶杯。
有人上门都是客,要赶紧请坐“倒茶”才是有家风礼仪的门户。
或是古风遗存,却也无从考究。
开门七件事,唯独茶上升到文化与精神,不同于油盐酱醋。
可出世,可入世。上至庙宇高堂,下可寻常烟火。
至清至净,至朴至拙,也可大俗大雅。
茶,是有魔力的。
因为要交作业,翻阅以前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://www.xihuangcaoa.com/szhj/11072.html


